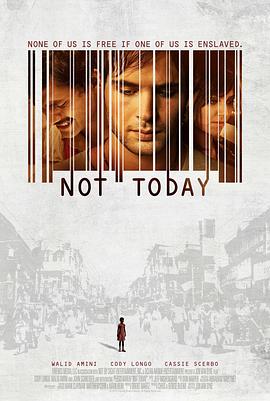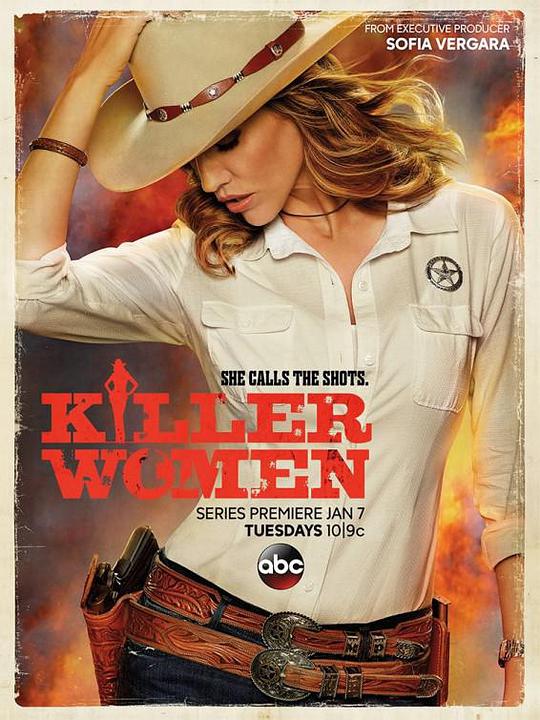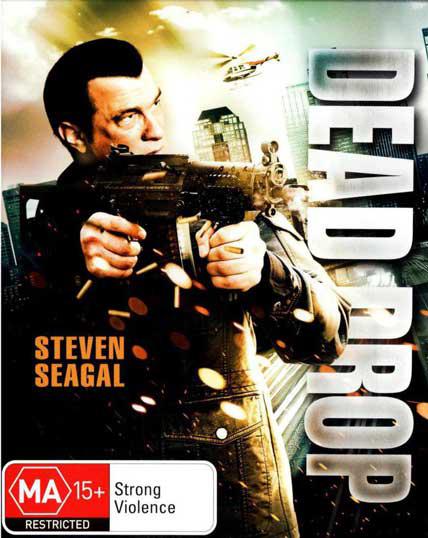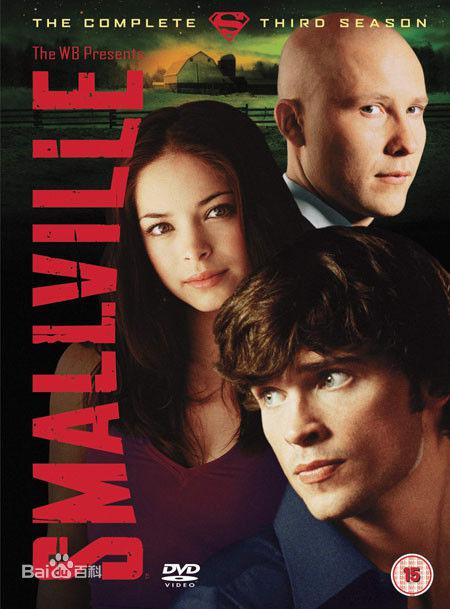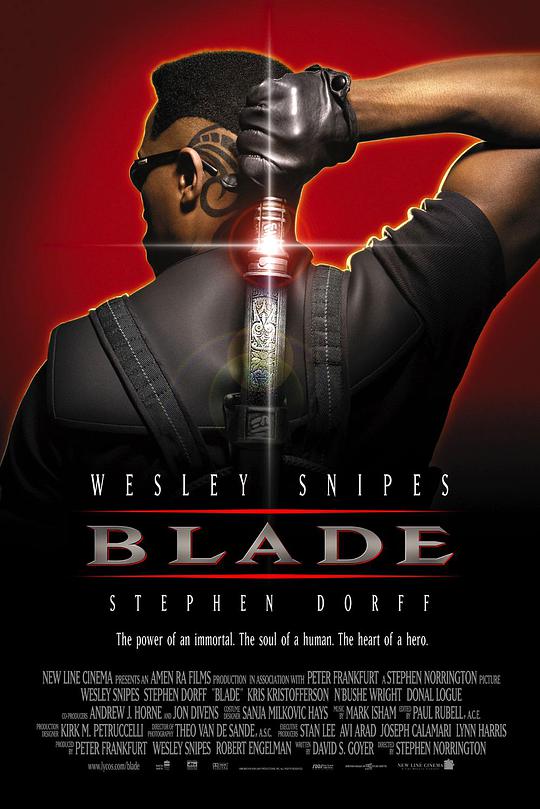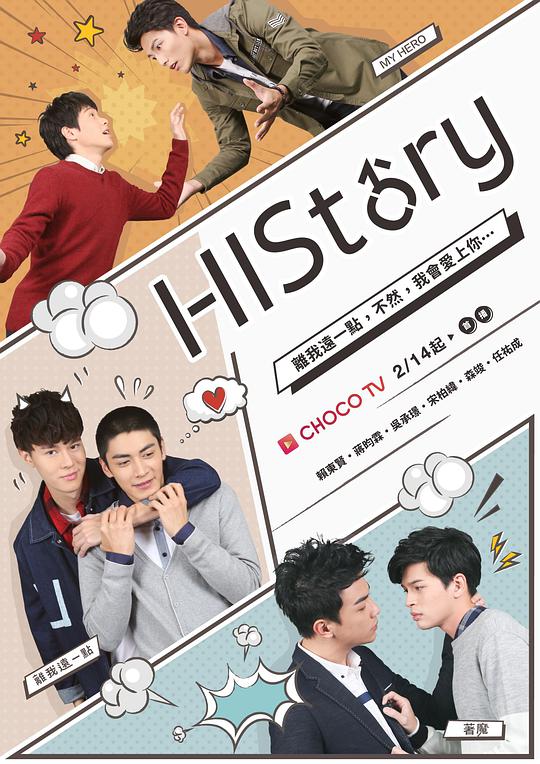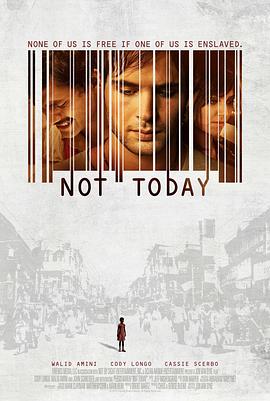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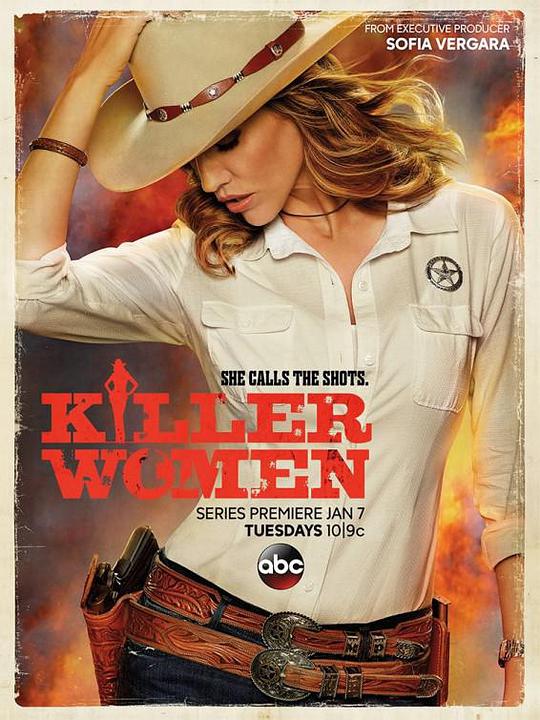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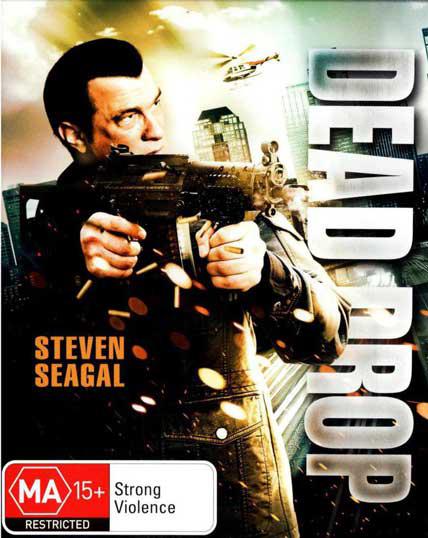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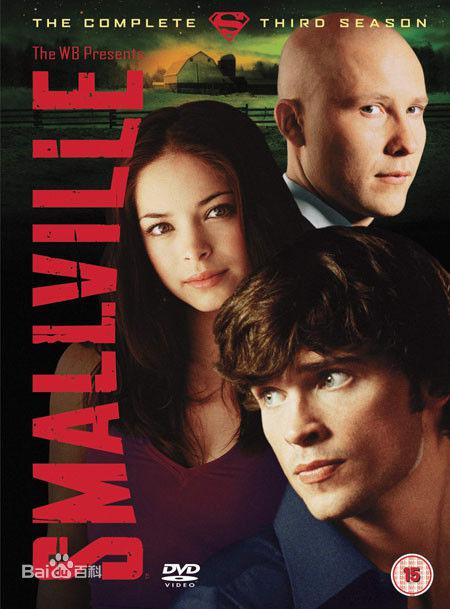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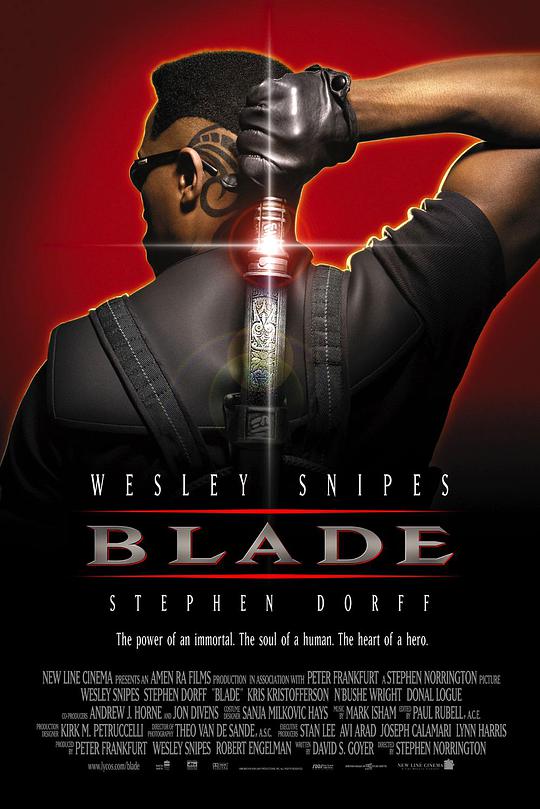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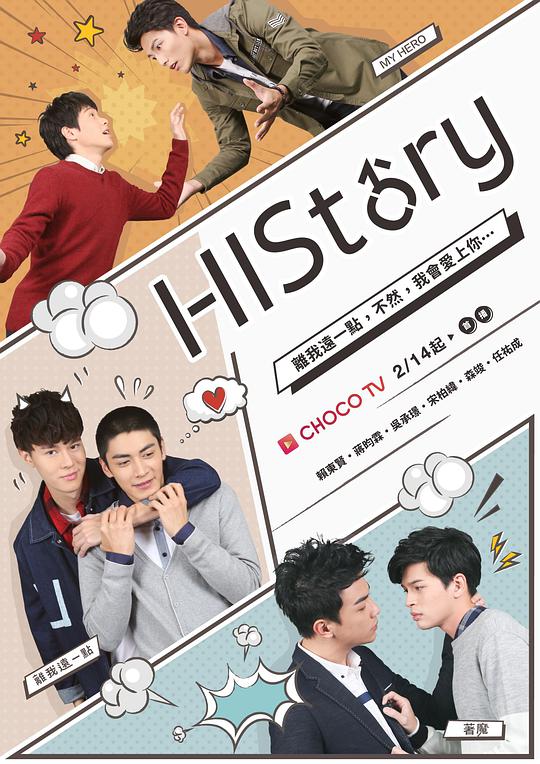
编者按
2025年11月,佐赫兰·马姆达尼当选纽约市长,成为该市历史上首位印度裔穆斯林市长。该事件不仅引发美国舆论关注,也意外唤醒了一段在印度公共记忆中逐渐被遗忘的历史。16至17世纪,古吉拉特穆斯林商人活跃于马六甲—东南亚贸易网络,将艾哈迈达巴德出产的纺织品运往海外换取香料,并通过价格战、操控港口权力等方式与荷兰东印度公司周旋,甚至借助悬挂对手旗帜规避禁运。18世纪莫卧儿帝国衰落后,博赫拉、梅蒙和科贾等社群依托以“jamaat”为核心的宗教社群组织,在孟买迅速崛起,成为当时印度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之一。19世纪以来,随着殖民扩张,该群体进一步走向海外,马姆达尼家族的迁徙轨迹正源自这一历史脉络。然而,20世纪泛伊斯兰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对立,使这段以海洋贸易、跨文化合作为核心的“世界主义”历史传统逐渐被身份政治叙事所遮蔽。马姆达尼当选后,印度人民党政客公开宣称“不会允许任何穆斯林成为市长”,恰恰反衬出作者的核心关切——当代印度的族群政治,正在不断侵蚀多元共存的历史记忆。本文的写作意图,正在于借由这一当代事件,重新召回被压缩、被遗忘的历史可能性。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纽约市长佐赫兰·马姆达尼。图源:路透社
从莫卧儿港口到荷兰战火,再到孟买的商人王朝,古吉拉特穆斯林曾塑造过整个印度洋世界——早在他们的一位后裔登上纽约舞台之前。
2025年11月4日,佐赫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当选纽约市长,在世界媒体中引起了意想不到的回响,对于一个美国城市的行政首长而言,这样的关注度实属罕见。但这位年轻的印度裔穆斯林,一位公开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所引发的轰动不过是一片更为古老的“海洋”中泛起的涟漪。
马姆达尼用古吉拉特语、孟加拉语、阿拉伯语、印地语、卢干达语和西班牙语发表演讲,他正是那个近乎被遗忘的、印度穆斯林世界主义精神的当代化身。他所属的古吉拉特裔穆斯林社区曾经挑战荷兰在印度尼西亚的霸权;也曾从日本延伸至阿拉伯世界,投资兴建学校、医院与印刷厂,更一度协助大英帝国巩固其在非洲的统治。时至今日,这段印度穆斯林的历史仍然回响——无论是在伦敦的高端拍卖行,还是在纽约的工人阶级聚居区,都能寻到它的踪迹。
一、印度洋中的古吉拉特人
本专栏的灵感源自一条颇为平淡无奇的X平台推文——该推文称,马姆达尼掌握多门语言的能力,若放在近代早期的东南亚香料贸易中,定能为他赚得盆满钵满。截至发稿,这条推文的浏览量已超百万,并获得5.4万次点赞,这一现象恰恰精准折射出古吉拉特穆斯林当年得以跻身国际贸易顶尖行列的核心优势。
X平台推文。图源:X网站
历史学家鲁比·马洛尼(Ruby Maloni)在其论文《16 —17 世纪的古吉拉特与东南亚贸易》中,将古吉拉特的重要港口坎贝(Khambhat)描述为“伸展出两条臂膀——一条朝向亚丁,另一条朝向马六甲”。当时,巴尼亚们(Banias,印度传统商人种姓)在东非、波斯湾贸易中尤为突出,而古吉拉特穆斯林商人则主导了马六甲贸易,他们将艾哈迈达巴德工坊生产的价格相对低廉的雕版印花纺织品远销至东南亚腹地,用以换取香料。
在这些商人中,地位最显赫的那批人实际上形成了若干商业世家,且与莫卧儿宫廷等势力联系紧密。不过,和古吉拉特的印度教徒、耆那教徒群体一样,他们的商业活动也带有浓厚的种姓式集体组织特征。
在苏拉特,这一切体现得尤为鲜明。作为印度西海岸或许最引人瞩目的港口,苏拉特汇聚着纷繁的语言——古吉拉特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乌尔都语、荷兰语、英语与葡萄牙语在此交织回荡,喧腾不息。尽管不同种姓与宗教之间壁垒清晰,无论是在印度教徒还是穆斯林的社群内部,古吉拉特商人都恪守着严谨乃至近乎严苛的行事准则。同时,在人际交往和商业关系中,他们共同的古吉拉特文化血脉又让他们养成了开放包容的世界主义气度。
历史学家贾韦德・阿克塔尔(Jawaid Akhtar)在其论文《莫卧儿时期商业社群的文化》中提供了若干例证。在苏拉特,亚美尼亚商人与帕西人及穆斯林存在商业合作;毗湿奴派的巴蒂亚人(Bhatias)尽管受制于禁止越海的宗教戒律,仍与穆斯林合伙拥有货物与船只。阿克塔尔援引档案性证据指出,一些巴尼亚男性曾采用穆斯林婚姻习俗,例如向妻子支付伊斯兰意义上的婚聘金(mahr)。此外,穆斯林与印度教商人还曾联合向莫卧儿当局集体陈情,表达其共同诉求。
1669年,有一次,苏拉特的卡齐(Qazi,执掌沙里亚法庭的伊斯兰宗教法官)强迫一位毗湿奴派巴尼亚商人皈依伊斯兰教,来自不同宗教背景的近8000名商人为了抗议这一侵犯商人特权的行为,迁往巴鲁奇(Bharuch)。
古吉拉特的穆斯林商人很快意识到,欧洲人正在威胁他们在东南亚的贸易优势。马洛尼指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多次提到与这些商人周旋的困难:他们不仅发动价格战,还设法把自己的人安插进港口管理层,与荷兰人正面较量。看起来,荷兰人几乎拿他们没什么办法,始终无法阻止古吉拉特穆斯林继续从事贸易。
柔佛苏丹国(注:16—18 世纪活跃于马来半岛南端及马六甲海峡一带的重要马来伊斯兰政权)欢迎商人哈吉·扎希德·贝格(Haji Zahid Beg)的船只入港,他公然无视荷兰的禁运,照常收购锡矿。马洛尼还写道,另一些商人干脆把货物装上英国船只;而苏拉特那位富可敌国的商人阿卜杜勒·加富尔(Abdul Ghafur),甚至在自己的船上挂起了荷兰国旗,以此规避限制。
直到荷兰人以武力控制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古吉拉特穆斯林才真正失去了在马六甲的优势地位。不过,到了那时,新的机会早已在别处悄然浮现。
科贾族女性|出自孟买妇女献赠给威尔士公主的一本画册。该画册收录了艺术家曼彻肖·法基尔吉·皮萨瓦拉(Manchershaw Fakirjee Pithawalla,1872–1937)创作的 13 幅描绘印度女性的全页水彩画。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二、“企业伊斯兰”的兴起
随着莫卧儿帝国在18世纪逐渐动摇并走向瓦解,旧有由商人巨头和商业世家维系的秩序也开始解体。苏拉特在屡遭马拉塔国王希瓦吉(Shivaji)劫掠的同时,又面临着来自东印度公司在孟买新建港口的激烈竞争。
博赫拉人、梅蒙人和科贾人这三个古吉拉特穆斯林社群,原本只是规模不大的商人群体,却在这一政治格局的变动中占据了有利位置。马姆达尼的家族,正是出身于其中的科贾人社群。
在其奠基性著作《没有过客之鸟:1800—1975年古吉拉特穆斯林商业社群史》中,历史学家迈克尔·奥沙利文(Michael O’Sullivan)指出,这三个群体的分布范围极为广阔:“东至乌贾因,西至卡拉奇,南至浦那,北至乌代布尔……因此,他们所覆盖的活动空间,据一位19世纪40年代的印度词典编纂者估算,比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还要大。他们共同的母语——古吉拉特语,成为中西部印度最主要的商业语言。”
博赫拉人、梅蒙人和科贾人虽然都在15 世纪左右改宗伊斯兰教,但他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传统却并不一致。这些社群内部存在不同分支,有的信奉逊尼派或什叶派传统,有的属于伊斯玛仪派,尊奉阿迦汗(Aga Khans);也有一些群体更强调地域出身,敬奉苏菲派圣徒。
然而,这些群体所共同拥有的,是一种称为贾马阿特(jamaat)的宗教—社群组织。奥沙利文将其形容为一种带有“企业化运作”特征的伊斯兰制度。简单来说,每个jamaat的成员都会共同管理和使用一部分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医院等。与此同时,一些极为富有、且往往身居重要宗教职位的成员,还各自掌控着私人的家族信托和公司。
奥沙利文指出,jamaat所提供的,是一套兼具组织性、排他性与解释权的制度机制,使这些社群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对伊斯兰实践的具体形态进行调整与诠释。借助这一组织形式,jamaat得以以其他印度社会机构难以比拟的速度,动员资本、人力资源,以及宗教解释上的灵活性。
从整体来看,这些古吉拉特穆斯林的jamaat社群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崛起为印度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力量之一。尽管在当今的公众印象中,它们往往被帕西人和巴尼亚企业家所掩盖,但在当时,古吉拉特穆斯林同样与马拉塔人和英国人周旋,从鸦片战争中获利,并很快转向各类商品的制造业,尤其是在孟买。
19 世纪 40 年代,古吉拉特穆斯林出资推动了早期的古吉拉特语印刷出版,其中包括面向中国等新兴市场的游记和文化介绍读物。随着财富不断积累,他们还修建了许多气势非凡的宅邸,例如锡德布尔(Sidhpur)的那些豪宅——如今大多已人去楼空。也正是古吉拉特人,或许比任何其他印度群体都更早,在东非为英属印度帝国建立起金融体系;马姆达尼的家族,正是沿着这一迁徙路径而来。
这一切共同促成了印度洋伊斯兰世界重心的一次决定性转移。正因如此,受到伊斯玛仪派科贾人尊奉的阿迦汗,才在印巴分治前将其宗教权威的驻地从伊朗迁至孟买。
锡德布尔,古吉拉特邦。图源:维基共享资源
三、被遗忘的普世主义
古吉拉特穆斯林所推动的伊斯兰实践,吸收了现代资本运作与财产继承的语汇,并在不断进入新的市场和文化环境的过程中,频繁分化出新的jamaat(贾马阿特)宗教—社群组织。
与此同时,正如研究者丹尼什·汗(Danish Khan)所注意到的,古吉拉特的穆斯林们在甚至还没有踏上美国国土之前,就已经在孟买获得了领导地位和影响力。他写道,“殖民印度的第一位穆斯林男爵是科贾人,第一位穆斯林文官(ICS officer)是苏莱曼尼博赫拉人(Sulaimani Bohra)。巴德鲁丁·泰比吉(Badruddin Tyabji)和拉希姆托拉·萨亚尼(Rahimtoola Sayani)是国大党最早的两任穆斯林主席。亚当吉·佩尔博伊(Adamjee Peerbhoy)则主持了穆斯林联盟在卡拉奇召开的第一次会议。”
然而,随着20世纪初泛伊斯兰主义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天平再次发生倾斜,那些以贸易与海洋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逐渐被围绕古老内陆王权想象所激发的政治怨恨所覆盖。
古吉拉特穆斯林的历史如今处于何种位置?马姆达尼的当选在多个层面上都显得意味深长。在孟买——古吉拉特穆斯林曾经的历史家园,一位印度人民党政治家在回应马姆达尼在纽约胜选时宣称:“我们不会允许任何汗(指穆斯林)成为市长。”
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古吉拉特穆斯林的历史,在现实政治中几乎已消失于激进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激进伊斯兰主义之间不断扩大的裂隙之中。仿佛在每一个新闻周期里,印度那些彼此交织的历史,都被进一步撕裂开来。
作者简介:阿尼鲁德・卡尼塞蒂(Anirudh Kanisetti),印度历史学家。他是《大地与海洋之主:科拉帝国史》(Lords of Earth and Sea: A History of the Chola Empire)和获奖作品《德干之主》(Lords of the Deccan)的作者,主持《印度回声》(Echoes of India)和《战争》(Yuddha)播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