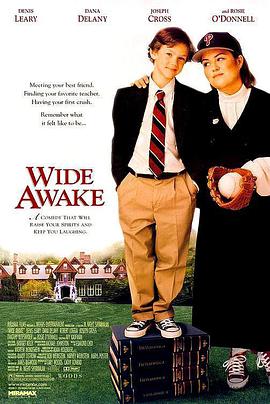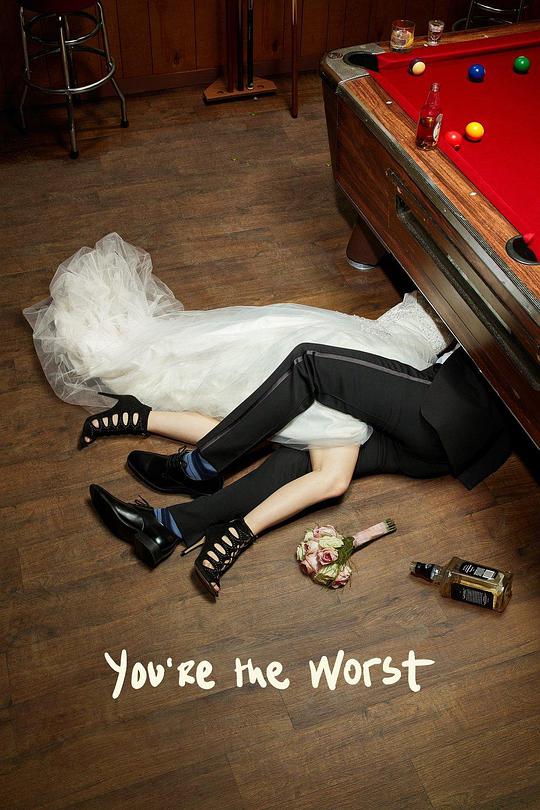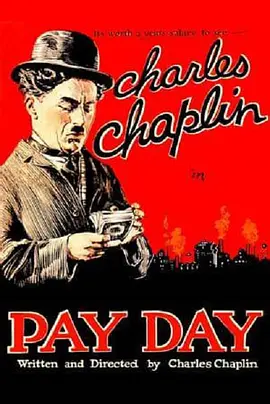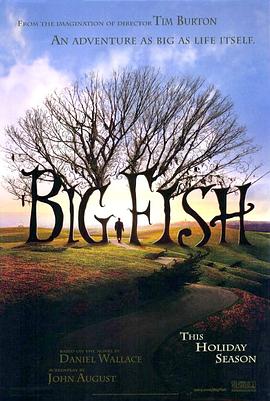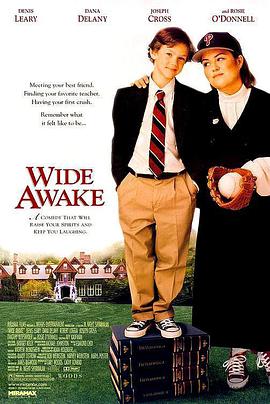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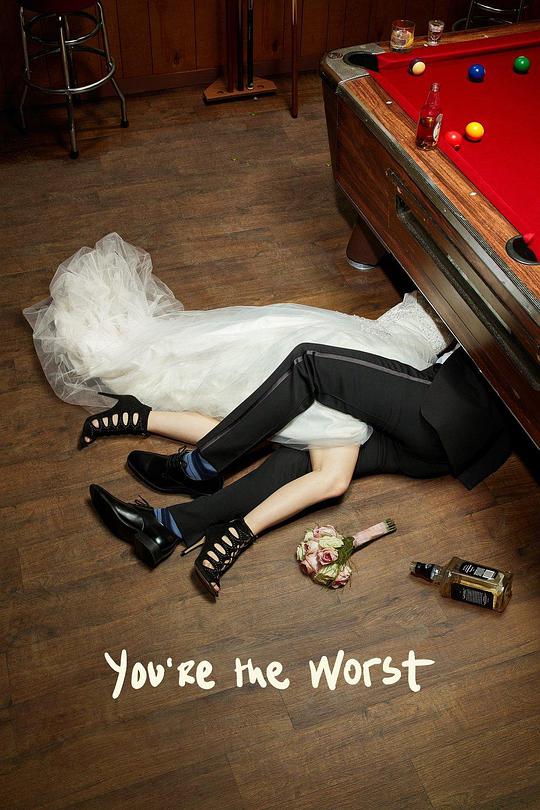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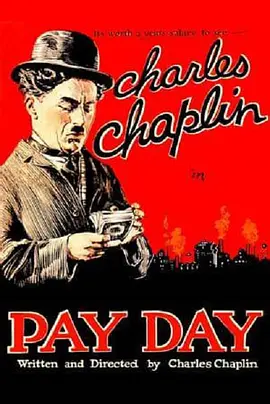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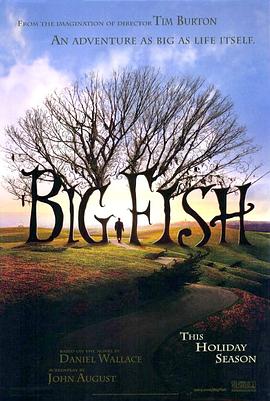









晨光爬上窗棂的时候,夜还恋在墙角。光与暗就这样抵着额,分不清谁在推,谁在让。桌上的茶烟,袅袅地、斜斜地,在亮处是透明的金,在暗里便成了青灰的絮——原来阴阳从不撕扯,只是温柔地交替着坐席。
壹·天地是个转不息的戏台
太阳登台总爱轰轰烈烈。先在东边云幔后抹腮红,猛地撩开幕——霎时千万支金箭齐发,射得露珠迸裂,射得江面碎成百万鳞甲。山醒了,把影子整匹整匹地往西边抛;鸟醒了,叼着光的碎片叽喳争抢。这是阳的性子,什么都亮堂堂地敞着,仿佛要把心都掏出来晒透。
月亮却是从水底浮上来的。先是一痕极淡的银,像谁遗落的指甲痕;继而慢慢胀、慢慢圆,圆成一面被呵过气的古铜镜。光也不急着泼洒,只是静静地渗——屋瓦白了,石阶青了,晾着的衣裳都成了悬空的魂。这时你才懂,阴不是暗,是另一种亮法:把锋芒都敛成柔晕,把声响都酿成寂静。
最妙是交界时分。夕阳在山梁上卡住了,半边脸红透,半边已灰青。归鸟的翅尖蘸着金,尾巴却拖进靛蓝里。妇人收衣裳,竹竿头还在光里,布角已浸入暮色。阴阳就在此刻交颈,不是打仗,是跳一场舞——光退三步,暗进两步,总留着些缠绵的余地。
贰·万物都在对影成双
你看那树。朝南的枝杈张狂些,叶密得像要滴下绿来;朝北的枝条谦逊些,疏疏地透着天光。可风一来,全都哗啦啦地翻手掌——正面是油亮的翠,背面是哑光的青。原来每片叶子都自带着阴阳,笑着把两面人生过完。
山更有意思。阳坡的草急着长,没到五月就抽穗;阴坡的苔慢性子,三年才铺满一掌绒。樵夫说:阳坡打柴,劈啪声都脆些;阴坡采菇,连呼吸都得放轻。可暴雨来时,阳坡的水急匆匆冲成沟,阴坡的泉眼却咕噜噜冒得欢——刚柔各有时辰,急缓自有道理。
水最是通透。浅滩处,卵石纹路看得真切,小鱼影子钉在沙上——这是阳水,什么都要说破。转到深潭,墨绿墨绿的一汪,丢个石子下去,闷声半晌才浮起几个泡——这是阴水,把秘密都沉在肚里。可浅滩养不活大鲵,深潭开不出菱花,它们还得连着、通着,才是一条活的河。
叁·人心里也住着日和月
少年时谁不是一团火?走路要带风,说话要撞钟,看山嫌山不高,看海嫌海不深。爱起来要把心剜出来,恨起来要烧了半边天。这是阳气太旺,从七窍往外冒,烫得自己都睡不着。
中年便学会了酿月光。话到嘴边含半句,事到临头让三分。开始喜欢旧东西——祖父的怀表走得慢,母亲的搪瓷缸有锈斑。夜深人静时,忽然听懂雨声是有韵脚的,一片叶子飘下的曲线,原来藏着数学也算不尽的柔。
可到底怎样才算正好?老祖母摇着蒲扇说:你看那煮粥——火太猛就糊底,火太弱就夹生。要守着灶,不时搅一搅。人这一辈子就是守一口锅,阳气是柴,阴气是水,熬到自己稠了、糯了,飘出淡淡的香,便是成了。
肆·世上最美的都在交界处
瓷器的妙处不在纯白,在釉色流动时,那抹偶然停住的青灰。画师的绝活不在满纸烟云,在留白处,让你听见山岚移动的声音。最好的琴声不是宫商尽奏,是弹到激昂处忽然一歇,余韵从寂静里重新生长出来。
江南的梅雨天最懂这个道理。雨下得人都快霉了,忽然太阳露脸,水汽蒸起来——整座城浮在半空,瓦是透明的,树是透明的,连卖栀子花阿婆的吆喝声,都裹着亮晶晶的水膜。这才知道,原来湿到极处,光会变得更珍贵;闷到极处,风会吹得更清醒。
连思念都是这样。月圆时想人,想的是热热闹闹的往事;月缺时想人,想的是零零碎碎的细节。等到不圆不缺的弦月夜,反而平静了——因为明白聚是阳,散是阴,圆缺本是月亮的一呼一吸。
伍·光阴在呼吸间流转
清晨菜场最鲜活。鱼在盆里甩尾,水珠溅到朝阳里成了碎钻;豆腐还冒着热气,白嫩嫩颤巍巍,像凝住的月光。卖菜阿婆的秤砣一扬一落:这边堆着沾泥的莲藕,那边摆着洗好的青芹——泥土的厚实与清水的灵透,都在这一杆秤上平衡。
黄昏茶馆最从容。紫砂壶嘴吐出的白气,曲曲折折升到房梁;说书人的惊堂木一拍,满屋子的影子都颤一颤。老先生蘸着茶水在桌上写:昼为阳,夜为阴。可你看这烛火——焰心最亮是阳,焰尾的蓝晕不就是阴?连一簇火苗都懂得自给自足。
忽然懂了古人为什么爱在廊下听雨。瓦是硬的,雨是软的;鼓声是急的,余韵是缓的。当千万颗雨珠同时敲击,反而听出一种大寂静——原来极动之中藏着极静,就像狂欢的深处住着孤独。
陆·平衡不是各占一半
真正的阴阳之道,哪是黑白平分那么简单?它是春日里,樱花开到最盛时忽然起风——粉雪纷扬中,你知道下一刻就要绿肥红瘦;它是盛夏午睡醒来的刹那,蝉鸣震耳,竹席的凉意却已爬上脊背。
就像酿酒,糯米要蒸透,酒曲要微凉;太烫杀曲,太冷僵米。守窖的人摸着坛壁说:火气在里头顶,阴气在外头包,两下里打架又拥抱,打着抱着就酿出了魂。开坛那天,第一缕香是冲的,第二缕就柔了——刚柔早已在黑暗里和解。
裁缝铺老师傅剪布料,光滑的缎子要配粗糙的里衬,挺括的西服要在肘部留些余量。“人都是一身矛盾”,他推推老花镜,“衣服得懂得迁就。”可不是么?最妥帖的衣裳,是让你忘了它的存在——阴阳调和到极致,便是浑成自然。
尾声·万物都在悄悄转化
起风了。晒着的被单鼓成帆,向阳那面金黄耀眼,背阴处还是潮润的蓝。孩子追着影子跑,不小心摔进光斑里——哭声刚起,就被母亲揽进荫凉中拍哄。你看,连疼痛都有阴阳:摔倒是阳,安抚是阴;泪水咸的是阳,怀抱暖的是阴。
茶凉了。茶叶沉在杯底,有的竖着,有的横着。竖着的还想再泡一会儿,横着的已睡熟了。我端起杯子,把最后一口喝尽——温的已凉,凉的又带些余温。原来喝到见底时,才尝出整杯茶的脾气。
窗外,路灯“啪”地亮了。不是骤然全明,而是从芯子里慢慢润出来,润成一团毛茸茸的橘黄。天还没有黑透,是那种鸭蛋青的底色,衬得灯光格外温柔。昼夜在此刻握手言和——就像世间所有对立的事物,最终都会在暮色里,找到共处的方式。
原来阴阳从未分离。它们只是光与影的舞蹈,呼与吸的缠绵,是你中有我的一场漫长厮守。当风穿过长廊,带着樟树香穿过夕阳最后一缕金线,你会听见天地间最古老的密语:
“我在这里。”
“我也在。”
永永远远,都在。